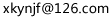名著中的名段摘抄 150-200字就行
作者&投稿:韦饶 (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)
~
工人工匠:
这人身体高大,半务农半是工匠,他扎了一条肥大的皮围裙,一直搭到左肩上,腹部鼓起来,皮裙里边装着一把锤子,一块红手帕,一个火药壶以及各种 各样的物什,像装在口袋里一样,由一条腰带兜住。他朝后仰着头,衬衣大敞着口,露出赛似公牛的白净脖颈。他长着两道浓眉,一脸很重的黑髯须,一对金鱼眼 睛,下颏儿尖尖的,还有一种难以描绘的在自家家中的神态。
——雨果《悲惨世界》
两个月的时光,他就似乎换了一副模样。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;浓密的黑发像毡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。由于活苦重,饭量骤然增大,身体看 起来明显地壮大了许多。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;右手背有点伤,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。目光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,像不起波浪的水潭一般沉静;上唇 上的那一撇髭须似乎也更明显了。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,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揽工汉子,和别的工匠混在一起,完全看不出差别。
——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
律师:
布雷木先生是有名的专办刑事案件的律师,法庭上人人都熟悉他……他是个身体高大而又相当瘦的人,肩膀很宽,脑袋很大,满头长着栗色的鬈发,一直 垂到上衣的领子上来,他老爱把它甩一甩,就像人们想象中的狮子甩他的鬃毛似的。他的脸刮得挺光,长着一张大嘴,一对相当小的黑眼睛几乎长在一起了。布雷木 先生穿着一件褐色的礼服,胸前扣上了纽扣,翻领上的纽扣眼里插着一朵玫瑰花蕾;下身穿着浅色的裤子。他胸前别着一枚宝石别针,人家可以看见它闪闪发光;他 坐下来脱掉手套的时候,又在他那只雪白的左手上露出了一只分量很重的图章戒指。
——[美]马克•吐温《镀金时代》
法官:
他是一个个子高大、穿得挺讲究、营养充足、持重谨慎的公司法律顾问。有一只眼睛给下垂的眼皮遮住了一半。他的肚子相当突出,给人一个印象:他要 不是在体格上,那么在心理上可活像一个气球,挂在什么非常稀薄的大气当中,只要任何一种早先法律方面的解释或是判例,轻轻给一吹,就可以要它东就东,要它 西就西。
——[美]德莱塞《美国的悲剧》
学生:
她那时正微低着头在看她的英语读本上的图片。漂亮的面容正似乎是风水先生手中的藤杖,它能使四面潜伏着的美立即显露出来。柔和的阳光在那一刹那 间似乎已变成了有知觉的生物;秋天也似乎忽然具有了一定的形象。像太阳约束着一切行星一样,这女孩使得天空、大气、光线和她身边的一切都围绕着她活动,而 她自己却颟顸地、沉默地坐在那里,看着一本教科书上的图片。
——[印度]泰戈尔《沉船》
约翰•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小学生,比我大四岁,因为我才十岁。论年龄,他长得又大又胖,但肤色灰青,一副病态。脸盘阔,五官粗,四肢肥,手脚大。 还喜欢暴食,落得个肝火很旺,目光迟钝,两颊松弛。这阵子,他本该呆在学校里,可是他妈把他领了回来,住上一两个月,说是因为“身体虚弱”。但他老师迈尔 斯先生却断言,要是家里少送些糕点糖果去,他会什么都很好。做母亲的心里却讨厌这么刻薄的话,而倾向于一种更随和的想法,认为约翰是过于用功,或许还因为 想家,才弄得那么面色蜡黄的。
——[英]夏洛蒂。勃朗特《简•爱》
艺术家:
他指挥的方法是那么自然而又柔和,看他的指挥就像听好的唱片那样,脚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打起拍子来了。他的手随着流畅的音乐自然而然地挥动着,这时,似乎他手中的指挥棒和那臂膀连同他的身影都融进了音乐之中,只有音乐而无其他,说不定这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吧!
——[日]小泽征尔《指挥生涯》
教师:
这位新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,就是面目的丑陋和身材的矮瘦。他的眼睛出奇的细小,里面滚转着一颗黄豆大的瞳仁,连颜色也是黄黄的。鼻子显得分外尖 削,嘴角边还生有一撮稀疏的黄须。因为年纪大了,腰背也就十分伛偻,仿佛永远俯屈着身子。看到他,很轻易使你联想到一只胆小的鼬鼠。不过,外表虽然引起人 家的尊敬,据说他的文理倒是很亨通的……
——王西彦《私塾师》
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,遇见一位国文先生,他给我的印象最深,使我受益也最多,我至今不能忘记他。
先生姓徐,名锦澄,我们给他取的绰号是“徐老虎”,因为他凶。他的相貌很古怪,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,很轻易成为漫画的对象。头很尖,秃秃 的、亮亮的,脸形却是方方的,扁扁的,有些像《聊斋志异》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。他的鼻子眼睛嘴似乎是过分地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。他戴一副墨晶眼 镜,银丝小镜框,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。
——梁实秋《我的一位国文老师》
作家:
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那位老人的形象:他穿着中间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,看上去很像30年代的长衫大褂,老人躬着背,走到方桌的一边坐下, 眼睛很细小,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浮肿,半耷拉着,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场随便碰上的任何一个老头,你简直难以想象他就是写了《激流三部曲》的大作家巴金。那天 正是阴天,窗外阴霾重叠,小小的客厅里十分严寒,他的儿女都去大串连了,可以想见老人的孤独和心境的凄惨。……
“你们怎么样,在学校好吧?”他嗫嚅地说。布满皱纹的脸上绽露出一丝微笑,正在这时,我看到了他的眼瞳中,发出了一道依然是聪明睿智的光线。
我们坐了一个小时,他似乎不愿提起他写的任何一部作品,因为那时报刊上正连篇累牍地批判他的书皆为大毒草,并且诬称他是由于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,才把自己的名字改作了巴金。
——[美]周励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》
渔民:
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。老渔民长得高大坚固,留着一把花白胡子。瞧他那眉目神气,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样,又清朗,又深沉。老渔民说完话,不等姑娘们搭言,早回到船上,大声说笑着,动手收拾着满船烂银似的新鲜鱼儿。
——杨朔《雪浪花》
这人身体高大,半务农半是工匠,他扎了一条肥大的皮围裙,一直搭到左肩上,腹部鼓起来,皮裙里边装着一把锤子,一块红手帕,一个火药壶以及各种 各样的物什,像装在口袋里一样,由一条腰带兜住。他朝后仰着头,衬衣大敞着口,露出赛似公牛的白净脖颈。他长着两道浓眉,一脸很重的黑髯须,一对金鱼眼 睛,下颏儿尖尖的,还有一种难以描绘的在自家家中的神态。
——雨果《悲惨世界》
两个月的时光,他就似乎换了一副模样。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;浓密的黑发像毡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。由于活苦重,饭量骤然增大,身体看 起来明显地壮大了许多。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;右手背有点伤,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。目光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,像不起波浪的水潭一般沉静;上唇 上的那一撇髭须似乎也更明显了。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,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揽工汉子,和别的工匠混在一起,完全看不出差别。
——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
律师:
布雷木先生是有名的专办刑事案件的律师,法庭上人人都熟悉他……他是个身体高大而又相当瘦的人,肩膀很宽,脑袋很大,满头长着栗色的鬈发,一直 垂到上衣的领子上来,他老爱把它甩一甩,就像人们想象中的狮子甩他的鬃毛似的。他的脸刮得挺光,长着一张大嘴,一对相当小的黑眼睛几乎长在一起了。布雷木 先生穿着一件褐色的礼服,胸前扣上了纽扣,翻领上的纽扣眼里插着一朵玫瑰花蕾;下身穿着浅色的裤子。他胸前别着一枚宝石别针,人家可以看见它闪闪发光;他 坐下来脱掉手套的时候,又在他那只雪白的左手上露出了一只分量很重的图章戒指。
——[美]马克•吐温《镀金时代》
法官:
他是一个个子高大、穿得挺讲究、营养充足、持重谨慎的公司法律顾问。有一只眼睛给下垂的眼皮遮住了一半。他的肚子相当突出,给人一个印象:他要 不是在体格上,那么在心理上可活像一个气球,挂在什么非常稀薄的大气当中,只要任何一种早先法律方面的解释或是判例,轻轻给一吹,就可以要它东就东,要它 西就西。
——[美]德莱塞《美国的悲剧》
学生:
她那时正微低着头在看她的英语读本上的图片。漂亮的面容正似乎是风水先生手中的藤杖,它能使四面潜伏着的美立即显露出来。柔和的阳光在那一刹那 间似乎已变成了有知觉的生物;秋天也似乎忽然具有了一定的形象。像太阳约束着一切行星一样,这女孩使得天空、大气、光线和她身边的一切都围绕着她活动,而 她自己却颟顸地、沉默地坐在那里,看着一本教科书上的图片。
——[印度]泰戈尔《沉船》
约翰•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小学生,比我大四岁,因为我才十岁。论年龄,他长得又大又胖,但肤色灰青,一副病态。脸盘阔,五官粗,四肢肥,手脚大。 还喜欢暴食,落得个肝火很旺,目光迟钝,两颊松弛。这阵子,他本该呆在学校里,可是他妈把他领了回来,住上一两个月,说是因为“身体虚弱”。但他老师迈尔 斯先生却断言,要是家里少送些糕点糖果去,他会什么都很好。做母亲的心里却讨厌这么刻薄的话,而倾向于一种更随和的想法,认为约翰是过于用功,或许还因为 想家,才弄得那么面色蜡黄的。
——[英]夏洛蒂。勃朗特《简•爱》
艺术家:
他指挥的方法是那么自然而又柔和,看他的指挥就像听好的唱片那样,脚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打起拍子来了。他的手随着流畅的音乐自然而然地挥动着,这时,似乎他手中的指挥棒和那臂膀连同他的身影都融进了音乐之中,只有音乐而无其他,说不定这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吧!
——[日]小泽征尔《指挥生涯》
教师:
这位新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,就是面目的丑陋和身材的矮瘦。他的眼睛出奇的细小,里面滚转着一颗黄豆大的瞳仁,连颜色也是黄黄的。鼻子显得分外尖 削,嘴角边还生有一撮稀疏的黄须。因为年纪大了,腰背也就十分伛偻,仿佛永远俯屈着身子。看到他,很轻易使你联想到一只胆小的鼬鼠。不过,外表虽然引起人 家的尊敬,据说他的文理倒是很亨通的……
——王西彦《私塾师》
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,遇见一位国文先生,他给我的印象最深,使我受益也最多,我至今不能忘记他。
先生姓徐,名锦澄,我们给他取的绰号是“徐老虎”,因为他凶。他的相貌很古怪,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,很轻易成为漫画的对象。头很尖,秃秃 的、亮亮的,脸形却是方方的,扁扁的,有些像《聊斋志异》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。他的鼻子眼睛嘴似乎是过分地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。他戴一副墨晶眼 镜,银丝小镜框,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。
——梁实秋《我的一位国文老师》
作家:
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那位老人的形象:他穿着中间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,看上去很像30年代的长衫大褂,老人躬着背,走到方桌的一边坐下, 眼睛很细小,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浮肿,半耷拉着,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场随便碰上的任何一个老头,你简直难以想象他就是写了《激流三部曲》的大作家巴金。那天 正是阴天,窗外阴霾重叠,小小的客厅里十分严寒,他的儿女都去大串连了,可以想见老人的孤独和心境的凄惨。……
“你们怎么样,在学校好吧?”他嗫嚅地说。布满皱纹的脸上绽露出一丝微笑,正在这时,我看到了他的眼瞳中,发出了一道依然是聪明睿智的光线。
我们坐了一个小时,他似乎不愿提起他写的任何一部作品,因为那时报刊上正连篇累牍地批判他的书皆为大毒草,并且诬称他是由于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,才把自己的名字改作了巴金。
——[美]周励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》
渔民:
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。老渔民长得高大坚固,留着一把花白胡子。瞧他那眉目神气,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样,又清朗,又深沉。老渔民说完话,不等姑娘们搭言,早回到船上,大声说笑着,动手收拾着满船烂银似的新鲜鱼儿。
——杨朔《雪浪花》